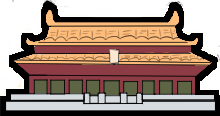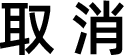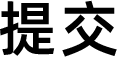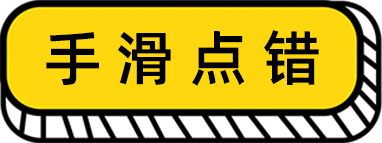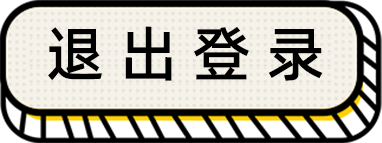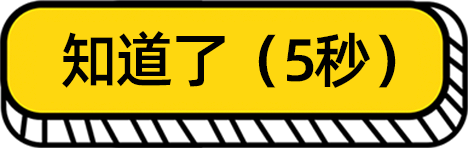明间的原状陈列,可以有两个方向:一为表现白天无所活动的状况,一即表现各种祭神礼节中之一种,陈列的属于后一种。在各种祭神礼中从所掌握的物品来考虑以表现每日朝夕祭为宜,但朝夕二祭不能同时进行,所以只表现朝祭。而夕祭神位平时就在北炕上,陈设的物品也可以同时存在。
朝祭的布置:故宫博物院从前有一个时期所陈列的坤宁宫祭神状况有个总的缺点,就是既非白天的状况,又不是祭时的状况。如今的布置是根据乾隆十二年《钦定满洲祭神祭天典礼》卷二坤宁宫常祭仪注、坤宁宫常祭祝辞、卷五祭神祭天器用数目、卷六祭神祭天器用形式图的记载,对原藏坤宁宫的物品和原祭神库物品加以研究核对,有些物品已残缺不堪无法修复,例如“镶红片金黄云缎神幔”和“背灯青绸幕”已经腐朽污损,则保存原件,用复制品陈列。
还有一些陈设,如:省猪(既杀猪)包锡红漆大桌,按制度应为两件(因为每次同时杀两只猪),但藏品只发现一张,原因是辛亥革命以后,每次改用一只猪⑩,所以多年来只剩下一张包锡红漆大桌了。朝祭神位所供的,据《满洲祭礼》载,为释迦牟尼(在髹金小亭内)、菩萨像、关帝像(画像轴挂神幔上),如今仅存关帝像一轴。据《满洲祭礼》载,“礼毕司香太监撤菩萨像,位关帝像于正中”,这时才开始杀猪。如今陈列的状况是炕前有两高桌,摆着盛猪的银里木槽盆,从供品前后次序说明猪肉摆上来之后,菩萨像当然是已经撤收了,所以如今朝祭神位的陈列中,只在神幔正中挂关帝像,和炕前的银里木槽是一致的。
夕祭所供的神根据《满洲祭礼》卷二夕祭仪的记载:“穆里罕神,自西按序供奉架上,画像神安奉于神幔正中,设蒙古神于左,皆于北炕南向。”从卷六“器皿形式图”供奉古神连靠黑漆座的图式和各种文件上都记载着蒙古神列于最末,可以断定原存北炕的连靠黑漆座上的两个绸制偶像就是蒙古神。
坤宁宫夕祭祝辞中“喀屯诺延为蒙古神”,所以这两件偶像就定名为喀屯诺延。在供夕祭神位绘花黑漆抽屉桌中原有画像一轴,当即是画像神。内容为七个盛装女子端坐椅上,上有飞鹊二只,下有清代服装的供养人二人。夕祭祝辞中有“纳丹岱珲”,《清史稿》礼志和《国朝宫史》解释纳丹岱珲为七星之祀,这个画像神是七个女子,可能就是纳丹岱珲。至于穆里罕神,估计原来可能是牌位而不是画像,在藏品中尚未发现此项物品。
煮肉蒸糕锅灶部分的布置:这一部分在正间之东的首间(即对着门的一间)向南的隔扇内。灶上有大锅三个,两只猪各占一锅,另一锅蒸切糕。
灶的北窗棂上挂着煮猪用的铁钩、铁勺、铁铲,窗台上放着照明用的铁板灯、木板蜡台。东墙上设着“东厨司命灶君之位”的木牌。隔扇外靠东墙设着“盛净水瓷缸”二件,放在红漆缸架上,两缸架之间放着一块圆形石头,叫作“打糕石”。据《满洲祭礼》卷五解释,打糕是“以稷米蒸饭,置于石,用木榔头打烂”,是粘糕一类的食物。
关于宝座的布置,《啸亭杂录》载:“大内于元旦次日及仲春秋朔,行大祭神于坤宁宫。钦派内外藩王、贝勒、辅臣、六部正卿吃祭神肉。上(指皇帝)面北坐……”《啸亭杂录》的作者是乾嘉时代的人,可以知道在那个时代以前,皇帝坐在南窗大床,而朝北。又据《曝直纪略》:“每年坤宁宫吃肉三次,枢臣皆与(按:指的是大祭,这和每日常祭只有少数侍卫参加吃肉的情况不同)。两宫祭神毕,太后坐北床,皇上坐南床,如太后不御坐则皇上坐北床。”从这个材料知道到了同、光年间,除了南床上安设座褥靠背隐枕一份宝座以外,在北床上又增设一份。这次陈列是按这种形式来布置的,坐北面南的一份最初曾经设在正间,后来经过文史馆衡亮先生提供照片核对后才改陈在西一间。还有南北两份宝座各安设铜座牛角灯两个于座褥左右,也是参考照片布置的。
总言之,坤宁宫原状陈列所表现的时间是包括清朝整个朝代的。在东暖阁内具体地表现同治、光绪婚礼期间内的状况,但并不排斥乾嘉以来遗留下来的陈设品。在明间内具体地表现举行朝祭的状况,这是坤宁宫从有祭神活动以来的原状,同时也不排斥同治以后南北对面设两份座位的状况。我们从一切能够找到的可靠史料中选择适当的内容,把原地点历史上积累下的室内陈设面貌,重新复原了。这次布置故宫中路的原状陈列自太和殿至坤宁宫都是在这种情形下进行的,这种陈列的方法,是否正确,希望得到各方面的指正。
衡先生曾经当过清朝的御前侍卫和都统等职,当年他每隔几天在月华门值宿。他说:“每逢值宿的日子到五更天的时候,就听见乾清门有太监喊‘请大人们吃肉’,当时的习惯语是‘叫肉’。所有乾清门的侍卫进来到坤宁宫门口领肉。那时候我是伊立答(满语即站班的头目),还有几个御前的和卓钦(即侍卫中管理蒙文翻译事)、太医院值班的,共六人。进门来,从南窗下每人拿一块毯垫(白心红边),地当中有一灯架子(尚在坤宁宫),在灯前放下垫子,向西一叩首,坐下。有太监给拿出一盘整方的肉,另有一人给盘内撒一把细盐,用手来撕吃,吃完把盘子一举,就有太监接过去,倘愿意再要也可以。”这是他谈每日吃肉的情况。